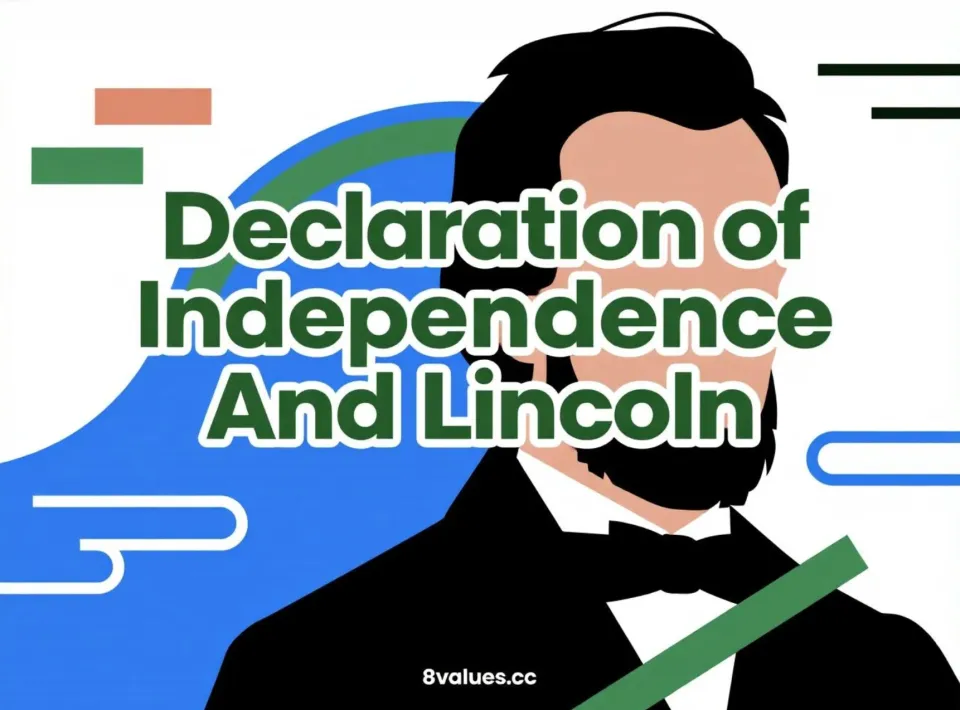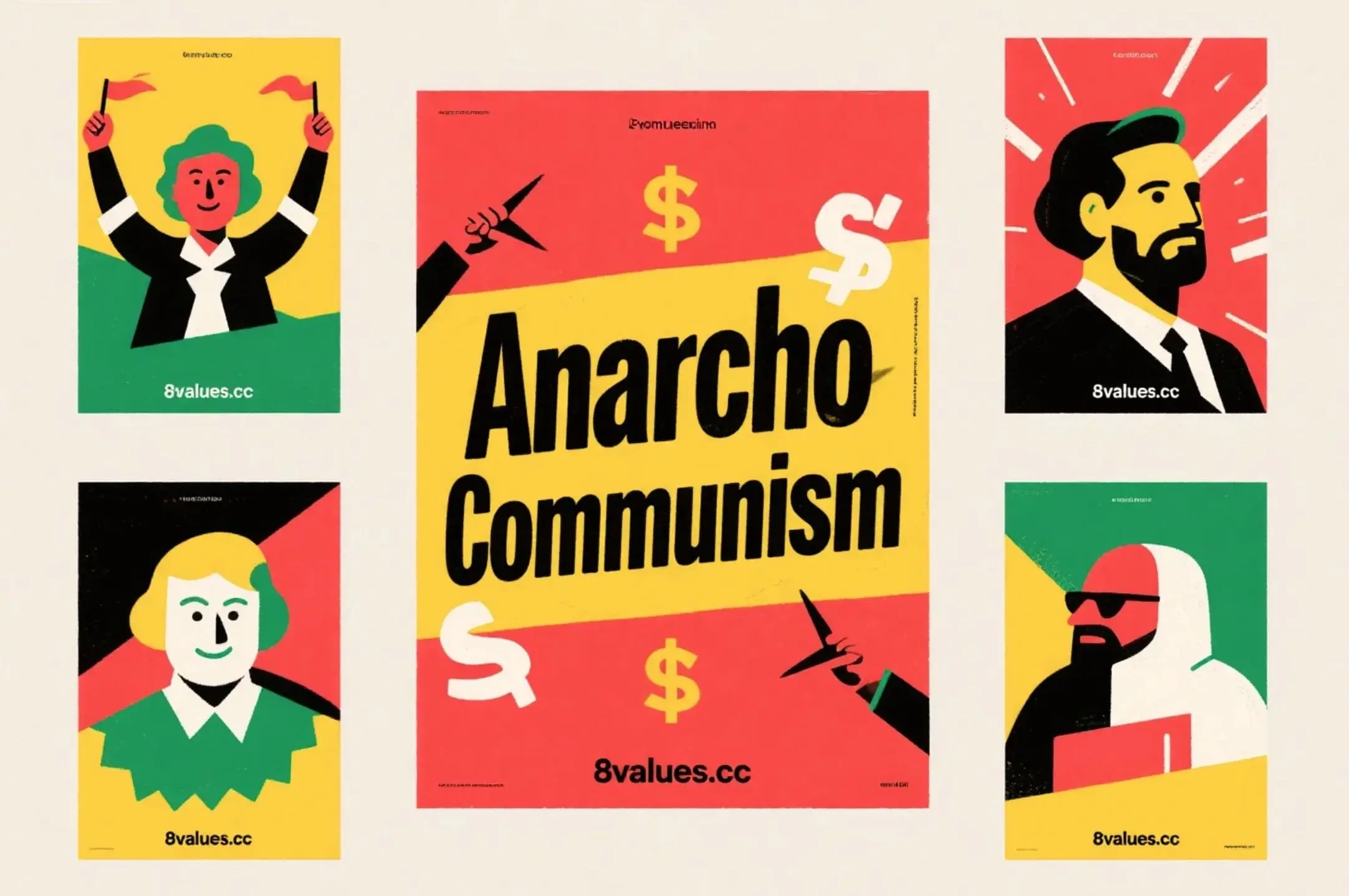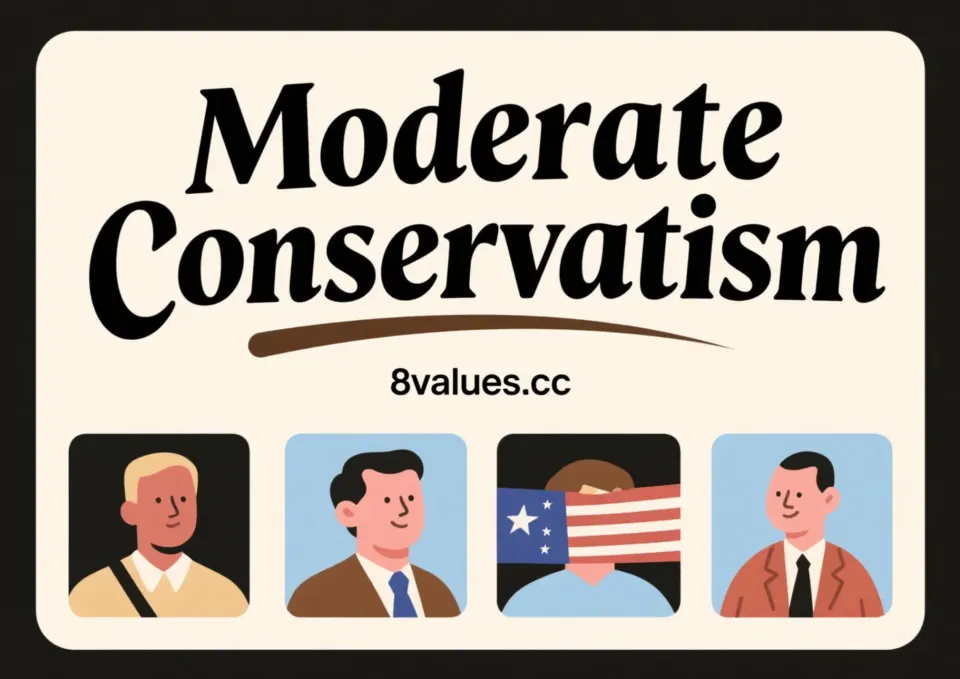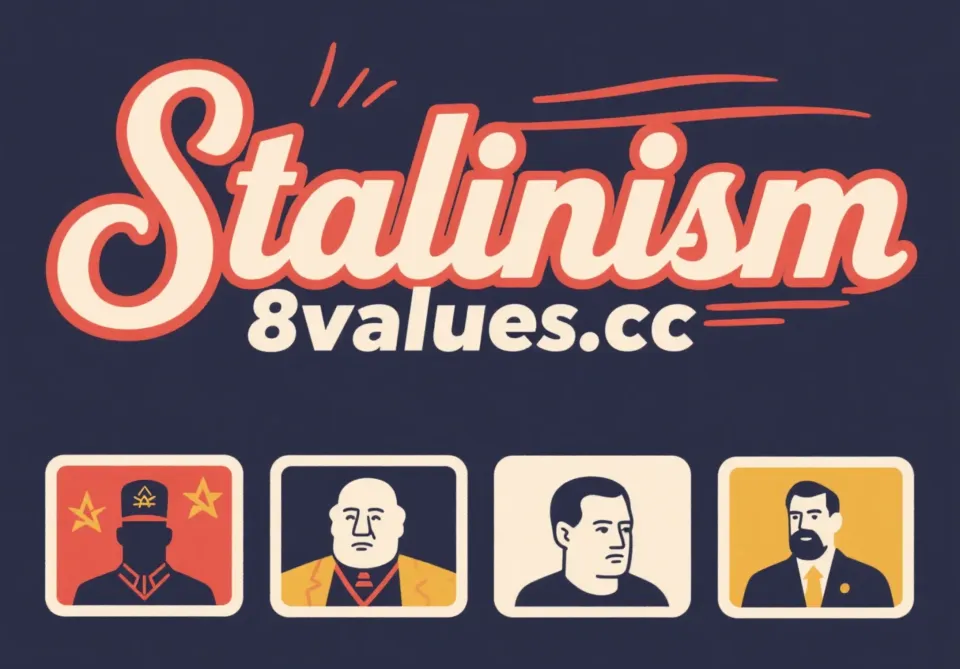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與林肯:廢奴及民權運動中的道德指南
深入探討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如何被亞伯拉罕·林肯重新詮釋為國家的道德標準,並在廢奴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和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中成為推動平等與自由的核心理念。
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美國最重要的立國文書之一,它莊嚴宣告了北美十三個英屬殖民地脫離大不列顛王國的統治,成為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份文件於1776 年7 月4 日由第二次大陸會議(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在費城批准通過,這一天也成為了美國的獨立日。儘管正式的法律獨立決議案(即李氏決議文)早在7 月2 日就已通過,但7 月4 日通過的這份公共宣言,因其深刻的政治哲學和雄辯的修辭,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件。這份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經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等人修訂的文件,不僅是為了向英國宣戰,更是為了向全世界解釋殖民地選擇分離的合理原因。
《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核心政治哲學
《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其第二段的序言部分而聞名於世,這段文字超越了殖民地時期關於英國憲法下的權利爭論,為後世奠定了美國政治思想的哲學基礎。
宣言的序言如下: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self -evident):人人生而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unalienable Rights ),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 )。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
啟蒙思想的深刻影響
《獨立宣言》的哲學基礎源於啟蒙運動。約翰·洛克(John Locke )對殖民地思想的影響最大。洛克在《人類理解論》(_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_)中提出人出生時心智如白板(_tabula rasa_),通過環境塑造個人,而非生來就具有等級差異。這直接挑戰了英國君主及其貴族階層宣稱的與生俱來的優越統治權。杰斐遜本人將洛克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三個人物之一”。
此外,宣言提出的政治哲學,即政府的權力來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以及人民有權改變或推翻壓迫性的政府,確立了一個公民民主的哲學基礎,保障了個人作為“人”所固有的權利。當政府一貫濫用職權、強取豪奪,旨在將人民置於絕對專制統治之下時,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
如果您對這些政治理念在現代社會的體現感到好奇,可以嘗試進行8values 政治價值觀傾向測試,探索您的個人價值觀與這些歷史原則的契合程度。
《獨立宣言》與奴隸制度的初始矛盾
儘管《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高舉“人人生而平等”的旗幟,但其誕生時期的美國社會,特別是南方殖民地,卻普遍存在奴隸制度,形成了深刻的道德矛盾。
初稿中的奴隸貿易控訴
托馬斯·杰斐遜是弗吉尼亞的奴隸主。然而,他在《獨立宣言》的初稿中曾加入一段對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激烈譴責。杰斐遜指控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對人性發動“殘酷的戰爭”,強行將無辜的非洲人民販賣為奴,甚至阻礙殖民地試圖立法廢除這種“可憎交易”。
然而,這段譴責奴隸制的文字最終被大陸會議刪除。刪除的原因是為了維護殖民地之間的團結。來自南卡羅來納(South Carolina)和佐治亞(Georgia)等以奴隸貿易為經濟重心的州份代表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此外,一些從奴隸貿易中獲利的北方州代表也反對這段文字。
英國保王黨人的質疑
這種矛盾立即引來了英國方面的批評。英國保王黨人(Tories)和前麻薩諸塞總督托馬斯·哈欽森(Thomas Hutchinson)質疑,一群擁有奴隸的國會議員,如何能在不釋放奴隸的情況下宣稱“人人生而平等”。英國廢奴主義者湯瑪斯·戴(Thomas Day)在1776 年寫道:“在自然界中,如果說有什麼事物是真正荒謬可笑的,那就是一個美國愛國者,一手簽署著獨立決議,另一手卻揮舞著鞭子恐嚇他受驚的奴隸”。
儘管存在這些矛盾,但《獨立宣言》的平等修辭本身,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了後來廢除奴隸制和民權運動中用於凸顯社會不平等的道德利器。
亞伯拉罕·林肯對《獨立宣言》的重新詮釋
在革命勝利後的數十年裡,《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文本本身並未受到太多關注,政治爭論主要圍繞憲法展開。直到19 世紀,隨著奴隸制度的爭議日益升級,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重新確立了《獨立宣言》的中心地位。
林肯將《獨立宣言》視為美國共和製度的道德憲章。他堅持認為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不只是歷史文獻中的一句話,而應該是國家政策和社會制度的指導原則。林肯認為,應將《獨立宣言》的原則視為解讀《美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道德指南。
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辯論
在1858 年與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著名系列辯論中,雙方就《獨立宣言》的意義展開了激烈交鋒。
道格拉斯斷言,“人人生而平等”僅適用於白人,其目的僅僅是為了證明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的合法性。
林肯則持有截然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宣言使用的語言是有意為之的普世性,旨在設定一個崇高的道德標準,供美國這個共和國不斷追求。
在1858 年10 月15 日於伊利諾伊州阿爾頓(Alton, Illinois)進行的最後一場辯論中,林肯對“平等”進行了精闢的闡述:
“ 我認為那份偉大文獻的作者意在涵蓋所有人( intended to include all men ),但並不意味著所有人在各方面皆平等。他們並不認為人們在膚色、身形、智力、道德發展或社會能力上完全相等。他們以相當清晰的方式界定了所謂人人生而平等的範疇——即在'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上平等,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們所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他們的目的僅是宣示此等權利的存在,好讓其實現可隨環境逐步推進。他們意在為自由社會立下一項指導原則(standard maxim),使之人所共知,常被仰望,持續努力( constantly labored for ),即使永遠無法圓滿達成,卻可持續接近( constantly approximated ),從而讓其影響日益深遠,讓所有膚色之人皆能獲益,提升人生價值與幸福。 ”
林肯認為,黑人與白人一樣有權享有《獨立宣言》所列的自然權利。他將美國的起源追溯到1776 年,並在1863 年的葛底斯堡演說( Gettysburg Address )中開宗明義:“八十七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大陸創立了一個新國家,其立國理念是自由,並致力於主張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
林肯的這一詮釋將《獨立宣言》提升為“第二次美國革命”的旗幟,塑造了美國人民對建國精神的理解,使宣言成為糾正憲法中不平等現象的道德力量。
廢奴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如何引用《獨立宣言》
在林肯之前,反奴隸制的廢奴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 )早已將《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視為重要的道德與政治資源。
廢奴主義者的精神支柱
對於廢奴主義者而言,《獨立宣言》是“兼具神學與政治意義的文本”。激進的廢奴領袖威廉·勞埃德·賈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曾將《聖經》和《獨立宣言》視為其哲學的“雙重支柱”。他宣稱:“只要我們國土上尚存《聖經》與《獨立宣言》,我們就不會絕望”。
賈里森和其他激進派人士甚至援引宣言中“推翻暴政”的權利,呼籲摧毀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的美國聯邦政府。
約翰·布朗的《自由宣言》
在南北戰爭前夕,激進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 )採取了更直接的行動。他在籌劃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起義前,於1859 年撰寫了一份《自由宣言》 * (_A Declaration of Liberty_),其寫作風格和用詞直接模仿*了1776 年的《獨立宣言》。
布朗的宣言明確指出:“當人類歷史的進程使一個被壓迫的民族有必要站起來、主張其作為自由共和國公民所享有的自然權利(assert their Natural Rights, as Human Beings, as Native & mutual Citizens of a free Republic )……他們應宣布推動此正義行動的原因”。該文堅稱“所有人皆生而平等”,並享有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份《自由宣言》有力地證明了《獨立宣言》的普世性語言如何被反奴隸制運動採納,成為爭取非裔美國人解放和正義的道德依據。
《獨立宣言》在民權運動與平權浪潮中的作用
《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平等修辭為19 世紀、20 世紀乃至21 世紀的社會和政治運動提供了共同的願景。
婦女權利運動
在1848 年,婦女權利的倡導者在紐約塞內卡福爾斯召開了美國歷史上首次婦女權利大會。她們起草的《婦女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就以《獨立宣言》為藍本,將開篇的平等原則擴展到女性群體:
“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男人與女人皆生而平等( 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 )。 ”
這一行動象徵著《獨立宣言》中關於自由與平等的概念被推廣到性別平權的領域,堅定地要求女性在社會與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特別是女性投票權。
二十世紀的民權運動
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民權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 )中,《獨立宣言》的核心語句再次被引用,成為爭取種族平等的強大道德工具。
1963 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 ("I Have a Dream ")演說中,直接引用了《獨立宣言》中的“信條”:
“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實現其信條的真正含義(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 ” ”
馬丁·路德·金將《獨立宣言》的承諾描述為一張“支票”,呼籲美國兌現對所有公民的平等承諾。他的演講強化了《獨立宣言》在推動反種族歧視和實現平等方面的象徵性地位。
此外,1966 年,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的創始人休伊·P·牛頓(Huey P. Newton)和鮑比·希爾(Bobby Seale)在其《十點綱領》 ( Ten-Point Program )中完整引用了宣言的序言。在當代,包括LGBTQ+權利運動在內的其他平權運動,也援引宣言中“不可剝奪的權利”適用於所有人的理念,作為爭取平等的基礎。
總結與當代價值:政治光譜的基石
《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起初是作為一份法律文書,宣告美國在國際法上的主權地位,以尋求外國政府的承認,特別是法國的軍事援助。然而,它的持久影響力並非來自其法律地位(它並非《美國憲法》那樣的法律文件),而是源於其政治哲學。
《獨立宣言》是“民主革命時代”的第一擊,影響了法國大革命、海地革命以及南美洲各國的獨立進程。
隨著時間推移,美國的政治生活和價值觀始終圍繞著《獨立宣言》所設定的崇高理想進行探索、辯論和實踐。它所包含的平等、自由和被統治者的同意等理念,構成了美國政治光譜的基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美國人為實現其“指導原則”而奮鬥。
探索這些歷史核心原則如何影響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有助於我們理解個人在當今社會中的政治定位。歡迎通過8values 政治價值觀傾向測試來深化您對這些原則的理解。